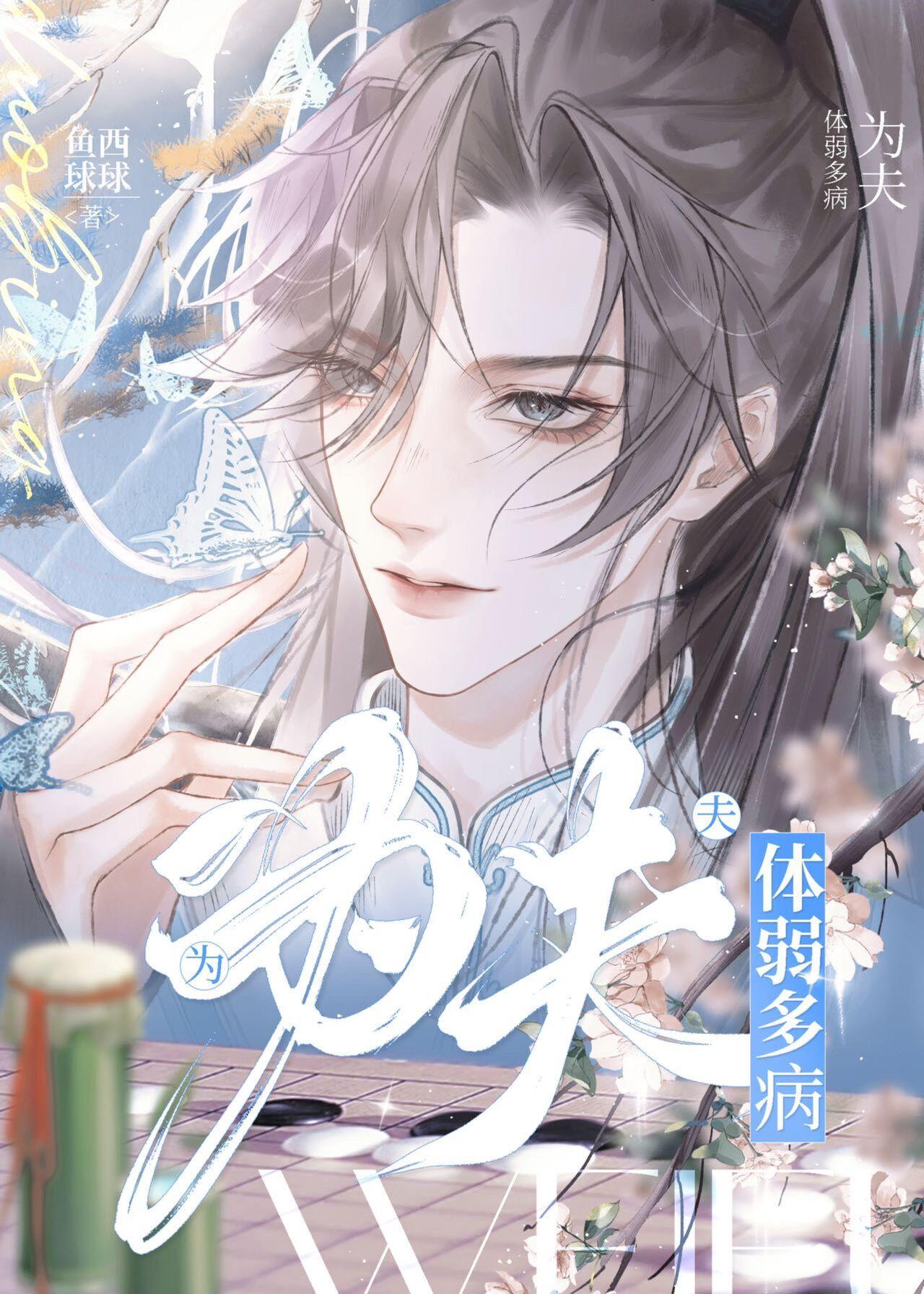精英小说>你和朝阳一起存在英文 > 旅途破冰(第2页)
旅途破冰(第2页)
等杨锦天过来,陈铭生掏出了羽绒服口袋里的矿泉水,“小天喝点水吧。”
杨锦天接过水,那瓶水上带着陈铭生淡淡地体温,就是那一抹淡淡地体温,却让杨锦天被一股暖流剧烈冲击,看着面前的两人,他忍不住说:“姐,我给你们照个相吧。”
陈铭生听了都很高兴,他扶着轮椅的扶手,从轮椅上站起来,杨昭很自然的递过肩膀,给陈铭生当拐杖,陈铭生借着力量,往旁边的栏杆边上一小步一小步地蹭,随着他的节奏,右边空荡荡地裤腿,无力的晃动着,他把空荡荡的裤腿向后掖在腰间,然后说:“小天,你给我们拍个半身像,把这个桥当背景。”
“嗯。”杨锦天找好角度,然后对他们说:“姐,你们靠近一点。”
杨昭往陈铭生身边凑了凑,把头斜斜地靠在陈铭生的肩膀上。陈铭生轻轻揽住杨昭的肩膀,杨昭环住陈铭生的腰,给他一个力量,支撑着他的平衡。他们两个人就像普通的游客一样,很放松,很惬意。他们看着对方笑,然后又一起向前看。
“特别好,我拍了啊,姐,再笑开心点,三二一——”
杨锦天跑过去,把拍的照片给他们两个人看,照片上,午后的阳光将两个人的剪影勾勒得相得益彰,背后的金门大桥,雄壮威武,前面两个人笑容灿烂,放松的靠在一起。杨昭很高兴,“小天,你回去照片传给我。”
“好的,姐,我到时候给你们洗出来。”
杨锦天又在旧金山玩了几天,杨昭带他逛了其他的几个有名的景点,还重点参观了斯坦福和伯克利,杨昭想用大学的氛围,好好熏陶一下杨锦天。
临行前,杨锦天专门到医院跟陈铭生告别,他买了一篮水果和一把鲜花。
期间,杨锦天和杨昭凑在窗户边上的小沙发上,翻看杨锦天手机里面的照片,杨锦天一张一张翻给姐姐看,两人一边看,一边回味这一趟旅途的难忘时刻,姐弟相处,说说笑笑,小小的病房里洋溢着简单的快乐。
陈铭生推着轮椅从洗手间出来,看到他们两个人凑在一起,轻松的神色,不仅自己也想挤进去看看,他推着轮椅来到两人边上,伸着头,想看。杨锦天看到,直接拉着杨昭重新调整位置,站在两人中间,翻着屏幕给两个人看。
翻着翻着,突然翻到了那两张远远的偷拍杨昭和陈铭生的照片,照片中姐姐笑得很灿烂,映着午后的暖阳,一双璧人的互动中,是掩藏不住地幸福。
“小天,你怎么偷拍我们。”杨昭抬眼看着弟弟。
杨锦天挠挠头,他的脸有些红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姐,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一趟旅行中,最美的风景。”
杨昭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听着杨锦天的话,陈铭生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他默默地推着轮椅,回到床边上,背对着两个人往床上转移。
护士进来给陈铭生挂水,他坚持半靠在床上,陪着姐弟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三个人相谈甚欢,杨昭看了看时间,然后说:“小天,要出发了。”
杨锦天站起来,他向病床走了两步,然后很认真地对陈铭生说:“哥,我回去了。”
话音一处,陈铭生和杨昭同时一顿,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杨锦天,杨锦天缓了一下,他继续慢慢开口“哥,你好好养病,等你和姐回去的时候,我去机场接你们。”
话语亲切自然,没有任何藻饰,有的只是发自肺腑的真诚。
这一声“哥”,叫得杨昭有点感动,以前杨锦天都是叫陈铭生“那个人”,杨昭讨厌这种叫法,她总喜欢跟在后面强调“他叫陈铭生”。后来杨锦天就叫陈铭生——“他”,而现在一句“哥”拉进了彼此。
杨昭懂得中国人特有的浪漫,这融会在中国人称谓之中,看似平常却不易察觉的情感,让杨昭第一时间,紧紧地捕捉到了。杨锦天没有叫陈铭生“姐夫”而是一句“哥”,她知道,如果是“姐夫”,更多的是一份客套、一份有些生分的距离感。“姐夫”——更多的是因为姐姐的身份,我承认你们的关系。
而一句“哥”却包含着杨锦天对陈铭生发自内心的认可。一句“哥”你除了是我姐夫,除了跟我姐姐的关系,我从心底里认可你,尊重你。一句“哥”诠释着——我除了姐姐,也认可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我的兄长,更是我的方向和榜样。
杨锦天看向陈铭生的眼神中少了原来的不屑和戾气,多了一份柔情和关爱,他走到陈铭生的床边,帮他把床尾的被角重新掖了掖,他看向陈铭生,露出了一个孩子一般无邪的微笑。
那一刻,杨昭感觉,他们的感情被弟弟肯定了,那种被肯定的温暖和幸福,像潮水一下,将她包围。
陈铭生也笑了,他回答道:“谢谢你,小天。一路平安,我们辽城见。”
“哥,辽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