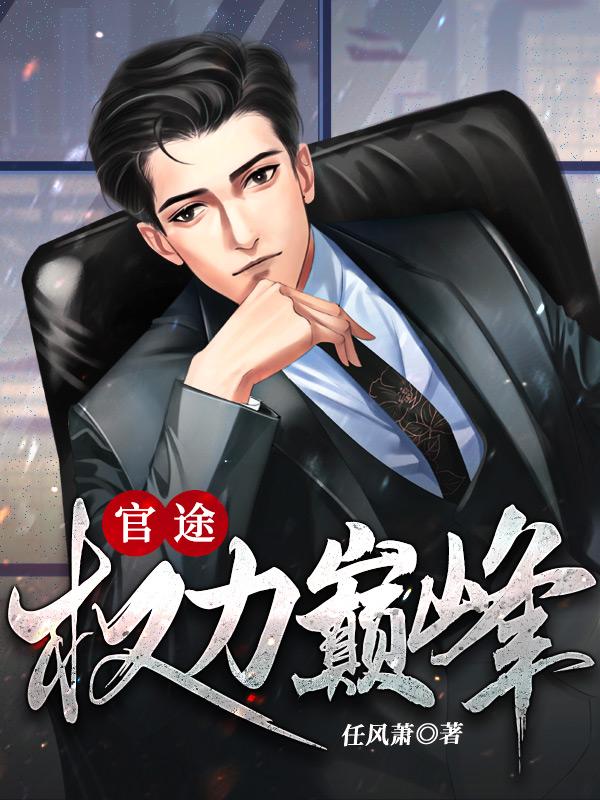精英小说>重启我的人生 > 第六十六章 秩序之外的光(第2页)
第六十六章 秩序之外的光(第2页)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秩序可能早在人类社会诞生前,就已经存在于人类个体内在的行为深层机制之中。
它不是文化,也不是制度,它是一种生物性自洽机制。
那天夜里,秦川写下长达七页的实验笔记,最后一句话是:
“系统可以被创造,但秩序必须被发现。”
而这句话,成为原像计划从哲学抽象迈入结构映射的分界点。
紧接着,实验组又开展第二阶段试验:群体非语言协同建模。
他们将四位实验者分别放入可听但不可见的四个独立房间,仅能感知到墙面微弱震动所带来的对方敲击频率,尝试在不说话、不见面、不知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共时节奏”。
这种实验被命名为“盲频协同”。
七天后,四人之间开始自然同步频率,并最终形成一个极为稳定的“六拍一休”节奏结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彼此在。”
这便是秩序的最原始形态。
不是依赖权威,而是依赖感觉。
而正是在这一系列实验完成后,秦川在某一夜悄悄写下一句话:
“人类并不一定需要上帝,但人类永远需要可触碰的意义。”
原像计划开展近一年以来,虽然从未发布任何正式研究成果、从未举办一次对外展示、也从不接受任何采访,但它的存在却像一种无法忽视的“暗能量”,悄悄地影响着外部世界。
起初只是一些高校学生在知乎、豆瓣、社交平台上讨论“行为自证系统”的可能性,后来则发展成数十家高校哲学、社会学、行为认知方向的独立研讨社团,开始自发研究“原像结构哲学”。
“它不是系统,而是一面镜子。”
“我们看不到它,但我们透过它,看到了我们自己。”
这些讨论没有明确结论,但都绕不开一个词——自生秩序。
而就在外部讨论逐渐升温之际,一家主流科技杂志突然刊出一篇题为《不可验证系统将如何改变社会信任结构》的长文,全文没有提及“原像”二字,却句句紧扣秦川提出的全部核心思想。
更诡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署名,是秦川曾经公开反对过的一位制度派技术学者。
“他在吸纳你的思想。”江允看到文章后皱眉。
“这很好。”秦川只说了这三个字。
“你不介意被他们包装、引用、甚至改写?”
“我不写给他们,我写给人。”
“可他们正用你的思想,建立另一个系统。”
“那不是我的错,是系统自己怕死。”
“什么意思?”
秦川笑了笑:“当旧秩序开始引用新思想自证正当性,它已经开始腐烂。”
这一场对话之后没几天,原像实验室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来访请求——
来自某大型国资背景研究机构,希望与原像“共建认知自律机制实验框架”,理由是“探索更具人本逻辑的秩序起源模型”。
原像成员听完这个申请文案后,集体陷入长时间沉默。
这封申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原像的“实验哲学”已经开始对现有体制构成影响力,甚至逼得一部分制度力量主动向其靠拢,以求“逻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