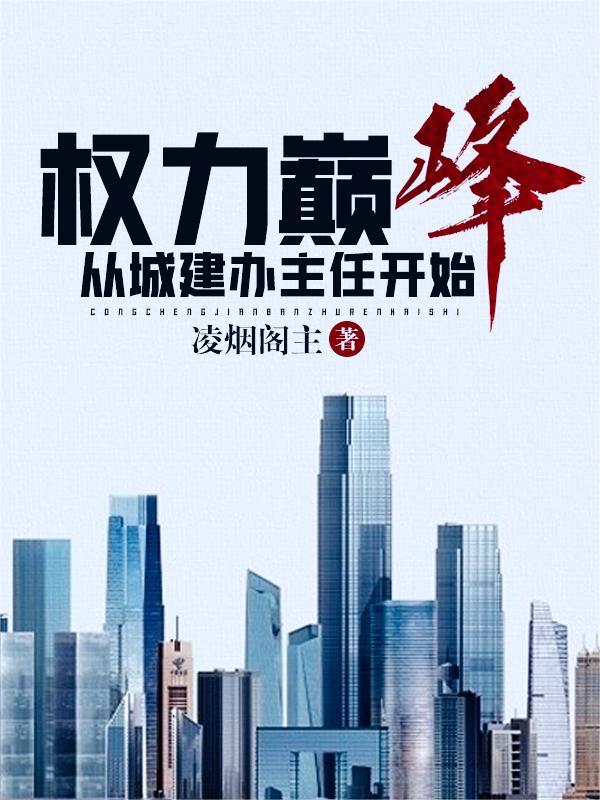精英小说>退婚太子后嫁给他弟 作者窃腰 > 第243章(第1页)
第243章(第1页)
迎面遇上卫衍,焦头烂额的几位大人忙停了嘴里的絮絮交谈,齐向卫衍行礼。
自从先太子被废,素来性情古怪的端王一夜之间突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朝臣们揣摩圣意,察觉皇帝大有以端王为继的意思,个个一板一眼,行礼行得格外毕恭毕敬。
卫衍只扫了一眼,脚步连顿都没顿一下,迳直越过几人,进了承平殿。
几位大人原地面面相觑,心里不约而同都在想这未来天子可不是个好相与的,短暂地为各自的前途担忧了一下,又脚步匆匆,为平叛的事各自劳心劳神去了。
皇帝捏着眉心,余光瞥见卫衍进殿,抬起眼看他。
“你夤夜进宫,恐怕不是为了来给朕分忧的吧。”皇帝脸上有些疲倦,但并无意外的神色,又低又缓地开口,三分的疲惫被低缓的声音放大了几分,倒显得仿佛疲累至极。
卫衍快走到殿中央停下,开门见山道:“我需要人手。”
皇帝一时有些恍惚——这孩子从小到大,从没主动跟说过他需要什么。
“又是为了那个盛媗吧。”皇帝摆了摆手,文公公会意,躬身退了下去。
端王府和卫府找人那么大动静,皇帝知道也不奇怪,卫衍看了一眼退去内殿的文公公,对皇帝道:“她现在在魏绍恒手里,找到她就找到了魏绍恒,这对皇上来说也是好事。”
皇帝不置可否,意有所指道:“要找到盛家丫头,你至少需要两个北城司的人手,那就不仅是人手了,是兵。”
卫衍盯着皇帝,立马明白了他什么意思:“怎么,我不做太子,你就不把兵给我,是吗?”
皇帝仍旧没有明确表态,却笑了一下,眼尾堆叠的皱纹显出他几分罕见的慈爱,却衬得他的笑仿佛是包容的取笑,在笑一个孩子的天真。
文公公从内殿出来了,手上捧着圣旨,两道。
卫衍瞳孔一缩,文公公已将圣旨送到了龙案上,皇帝拿起其中一道圣旨,像是搜肠刮肚重新打起了十二分的精力,脸上的疲惫突然一扫而空,沉声对卫衍道:“这是册封安定郡主的圣旨,你接了受立太子的旨意后,朕会给你兵权,而后命人到盛府宣旨,等盛景聿接了这道旨,城门自会打开,你便可顺利出城去救人。”
卫衍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他早想到要拿兵权不会容易,做太子便做太子,反正可以禅位,再不济还可以再废一回太子,又有什么了不得的?
可他没想到,皇帝还有一道圣旨,而一旦盛家接了旨,盛媗受封安定郡主既成事实,将来就再无可更改。无论谁做太子,她都只能是他的义妹,而郡主封号,除非犯下大罪,轻易也不可废。
卫衍几乎是咬着牙挤出了声音:“你早知道魏绍恒会对她下手!”
若非皇帝默许,废太子岂能轻易逃出雍王府。这一逃,遵、亭两州叛乱,盛媗被掳失踪,而最后的结果,无外乎是魏绍恒一直以来隐藏在暗中的势力在这次朝廷早有防备的叛乱中被全数歼灭,叛军掀不起大的风浪,最坏也不过是盛媗身死。
对皇帝来说,这个最坏的结果,何尝不是他心中一箭双雕的最好结果。
既为卫衍扫清了先太子的残余势力,使朝廷安定,又除去了卫衍感情上的最大牵绊,使君心再不受人动摇。
皇帝自龙座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对他怒目而视的儿子,语重心长道:“朕是为你好,你若不是非要执迷,朕也不愿意看到忠臣之后有此境遇。”
“呵。”卫衍冷笑出声,“你究竟是为我好,还是为了你魏氏的江山!”
“承砚……”
“臣接旨!”皇帝皱眉话没说完,卫衍蓦地单膝跪下,膝盖磕在地面“砰”一声响。
“……”皇帝一时愣住,没想到卫衍这么容易就肯妥协。
他长久地凝视着跪在殿中的人,青年低着头,只半露出斜飞入鬓的长眉,锋利得像一把闻血出鞘的长剑。
良久,皇帝朝文公公摆摆手,缓缓松下一口气道:“宣旨吧。”
宣德二十七年,四月十一丑时,大嵂新封端王为太子,自此揭开了一个震惊全国的身份秘密。
文公公捧着册封安定郡主的圣旨,早已经往盛府去,摘下面具的卫衍紧握着手里册封太子的圣旨,终于从皇帝手中拿到了虎符。
青年阴恻恻地看向鬓发微白的帝王,紧攥圣旨和虎符的手握得骨节森白,无法抑制的微微战栗着,皇帝还想说什么,青年转过身,一言不发疾步离开。
目的达到,皇帝望着青年瘦长的背影沉默片刻,到底松下一口气。
然而,这口气刚松下来,走到门口的卫衍突然停了脚步,一动不动定了片刻,慢慢转回身,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