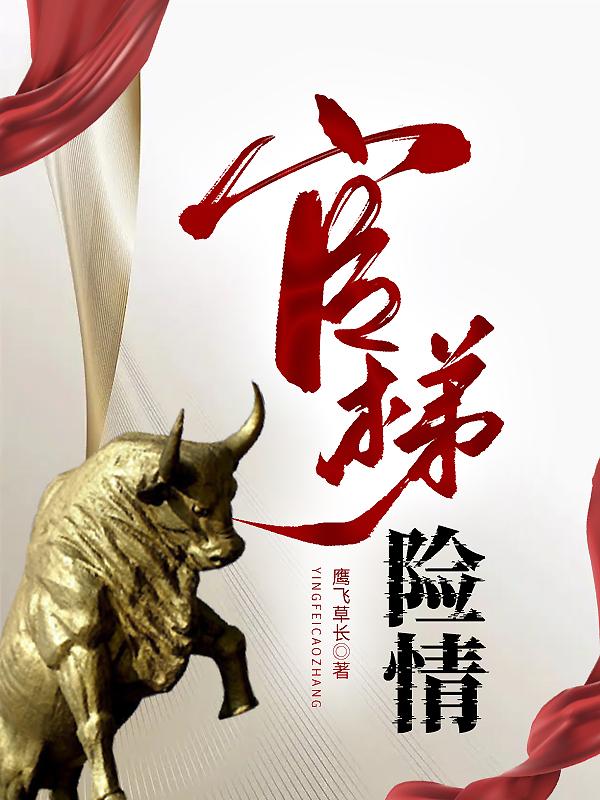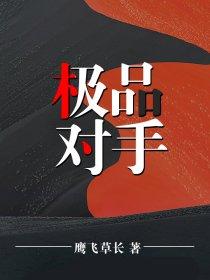精英小说>寒门仙途百度百科 > 第一章 狭小出租屋(第1页)
第一章 狭小出租屋(第1页)
2025年4月16日,春寒料峭。
铁架床的吱呀声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格外清晰。陈默蜷缩着翻了个身,生锈的床架立刻发出抗议般的声响。他盯着天花板上渗水的霉斑,听着厨房传来母亲压抑的咳嗽——凌晨五点,母亲又在熬中药了。
“小默,该起床了。”母亲的声音混着中药的苦涩飘过来。陈默摸黑穿上校服,袖口磨得发亮的布料蹭过床头的铁皮柜,柜角还粘着他去年贴的励志便利贴,边角已经卷翘,“考上华清,带爸妈住大房子”的字迹被潮气晕染得有些模糊。
出租屋被一张木板隔成两半,里间是父母的床,不足两米宽,父亲平躺时剧烈的咳嗽声会震得木板轻颤。陈默蹲在“客厅”的折叠桌前早读,桌面坑洼处用课本垫着,否则钢笔水会顺着倾斜的木纹晕开。窗外飘来早餐车的葱花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昨天剩下的三块钱,够买两个素包子。
“咳——”里间突然传来父亲压抑的闷咳,像破旧风箱在漏风。陈默听见母亲慌乱的脚步声,接着是搪瓷缸碰撞的脆响,“老陈,把这口梨汤喝了。”父亲常年在工地搬砖,去年秋天摔断了腰,赔偿款至今没拿到,潮湿的出租屋让他的旧伤反复发作,每到阴雨天气就咳得睡不着。
晨光从破了角的窗帘钻进来,照亮墙根处摞着的蛇皮袋——里面装着全家的家当。陈默的目光落在蛇皮袋上歪歪扭扭的“陈家”二字,那是父亲用红油漆写的,如今已经褪色剥落,像道未愈合的伤口。
“该上学了。”母亲掀开布帘,鬓角的白发在晨光里格外刺眼。她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昨晚剩下的半碗米,“中午别买饭了,妈给你带米糕。”陈默点头,视线掠过母亲洗得发白的围裙,口袋里露出半截中药包——那是父亲的药,母亲总说自己“身体好,不用补”。
路过里间时,陈默看见父亲蜷缩在床角,脊背弓得像张旧弓,工牌还挂在床头,“宏达建筑”的logo已经磨得看不清字。他突然想起上周在工地看见的场景:父亲蹲在脚手架下啃馒头,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落在未干的水泥地上,像道被踩进尘埃里的伤疤。
“路上小心。”母亲在门口塞给他一把伞,伞骨断了两根,用铁丝缠着。陈默刚踏出房门,楼道里的声控灯突然熄灭,黑暗中他撞上堆在墙角的蜂窝煤,煤灰扑簌簌落在校服上。他蹲下身捡拾滚落的煤块,指尖触到粗糙的表面,忽然想起父亲手掌上的老茧。
走到巷口时,早餐车的老板正掀开蒸笼,白汽裹着肉香涌出来。陈默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最终转身走向公交站台。校服口袋里硬硬的东西硌着大腿,他知道那是母亲偷偷塞进去的玉佩——说是奶奶留下的,让他“贴身带着保平安”。金属的凉意透过布料传来,他忽然想起昨晚看见母亲对着玉佩发呆,灯光下,玉佩表面的纹路隐约像座古老的道观。
公交站牌的铁皮在晨风中摇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陈默盯着站牌上的“华清大学”站,那是他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公交车进站时,他摸了摸裤兜,那里装着昨晚写好的简历——十六岁的高二学生,兼职洗碗工、发单员、便利店理货员,每一份工作都在深夜或周末,像他贴在课桌上的课程表,密密麻麻,不留空隙。
公交车在坑洼的路面上颠簸,陈默靠窗而坐,看着街边的广告牌闪过。某块电子屏突然故障,雪花点中浮现出模糊的古建筑轮廓,像极了他昨晚梦中的古巷。他揉了揉眼睛,再看时,屏幕已经恢复正常,上面写着“玄门商会春季拍卖会”,配图是块泛着微光的古玉。
校服口袋里的玉佩突然发烫,陈默慌忙按住,掌心触到凹凸的纹路,竟与屏幕上的古玉纹路隐隐重合。公交车在十字路口急刹,他的额头撞在玻璃上,却顾不上疼痛,视线死死盯着电子屏——画面里的古玉,分明和母亲给他的玉佩一模一样。
到站的提示音惊醒了他。陈默下车时,发现校服口袋被磨出个小洞,玉佩的棱角露在外面,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他低头整理时,忽然看见地面上有片水洼,倒映出自己的影子:校服领口磨得发白,书包带缠着胶带,却挺直了脊背,像棵在石缝里扎根的小树。
巷口的老槐树在风中轻晃,陈默走过时,一片泛黄的树叶落在他肩头。他伸手拂去,忽然听见树后传来窸窣声,转头看见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对着手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确定是那孩子?玉佩在他身上?”
公交车的尾气混着灰尘涌来,陈默咳嗽着加快脚步。他不知道,就在他转身的瞬间,西装男人从树后走出,指尖摩挲着枚刻满符文的玉简,玉简表面,“太虚观”三个字正在晨光中若隐若现。
出租屋里,母亲掀开床垫,露出藏在下面的铁皮盒。盒底躺着张泛黄的照片,二十年前的冬夜,年轻的父母抱着襁褓中的婴儿站在古巷口,身后的老槐树上挂着冰凌,树旁的石碑上,“太虚”二字清晰可见。
风穿过破旧的窗棂,掀起桌上的课本。陈默的笔记本上,最新的一页写着:“4月16日,父亲咳血三次,母亲偷偷掉眼泪两次,我攒了376块钱,离手术费还差9234块。”字迹工整得像是用尺子量过,最后一行画着个小小的太阳,边缘带着锯齿,像团倔强的火苗。
晨雾渐散,巷口的电子屏突然闪烁,广告画面切换成“玄门商会诚聘实习生”,配图是只泛着红光的手掌,掌心纹路与陈默校服口袋里的玉佩纹路,分毫不差。
(第一章完)